- 積分
- 354
- 經(jīng)驗
- 點
- 威望
- 點
- 金錢
- 兩
- 魅力
- 點
- 金幣
- 元
- 性別
- 保密
- 在線時間
- 小時
- 注冊時間
- 2014-11-27
- 最后登錄
- 1970-1-1
|
馬上注冊,結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讓你輕松玩轉社區(qū)。
您需要 登錄 才可以下載或查看,沒有帳號?點這里注冊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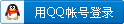
x
2月的最后一天,沉寂了一年的柴靜通過互聯(lián)網(wǎng)推出公益之作《穹頂之下》,聚焦大眾熟悉又陌生的霧霾問題。
柴靜女兒還未出生,就被診斷患有良性腫瘤,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術。所幸,手術非常成功。之后,柴靜辭職,全心照顧孩子。過程中,她對霧霾的感受愈發(fā)強烈。
“這是我和霧霾的私人恩怨。”柴靜說,“早上起來,我有時會看到女兒站在玻璃窗前用小手拍著,用這個方式告訴我她想出去玩。這一年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為了回答將來她會問我的問題,霧霾是什么?它從哪來?我們怎么辦? ”
有了這份情感驅動,母親柴靜,而非記者柴靜,展開了這項年度調(diào)查。
穹頂之下,我們每個人都在呼吸空氣。這是我們每個人與霧霾的私人恩怨,這個視頻,值得你認真看完!
柴靜,著名傳媒人,前央視主持人,記者。北京大學藝術碩士,曾長期制作污染治理報道如《山西:斷臂治污》《事故的背后》《塵肺病人維權調(diào)查》等,獲選2007“綠色中國年度人物”,中國環(huán)境文化促進會理事。2014年初從央視辭職,2015年初推出空氣污染深度調(diào)查《穹頂之下》。
這一年,我所見證的“柴靜與霧霾的私人恩怨”
文:南方周末記者 汪韜
今天上午,柴靜關于霧霾的紀錄片終于登出了,名字叫《穹頂之下》。
昨夜00:13,我正在收拾行李,收到了柴靜的消息,她淡淡地說:“應該明天上午發(fā)。晚安。”
我想,柴靜這一夜應該沒有安睡。
她說,可能像你說的,不在霧霾天發(fā)出,片子不會引起大家的關心。也可能播出后會有很多想到不到事情,但是它有它的命運了。
我也沒有安睡。這個保守了一年的秘密終于要公開了,而柴靜和我都不知道秘密公開之后會發(fā)生什么。
作為南方周末的環(huán)境記者,2011年秋以來,我一直在寫大氣污染的深度報道,并笑稱要做“最大氣的記者”。2014年5月,在環(huán)保部的一次會議上我遇到了柴靜,互留了聯(lián)系方式后,她時常和我探討一些大氣污染的問題,要一些專家的聯(lián)系方式。
我沒有對別人說起柴靜在關注霧霾的話題。這是記者之間最常見的交流,我并不感到驚訝。后來聽說她當了媽媽后,對于環(huán)境和食品安全問題越發(fā)關注。這正是我們南周綠色板塊關注的領域,我很欣慰。只是覺得她太認真了,大氣污染的各個領域都要涉及,做了一年,竟也沒有看到報道。
而直到2015年1月,我被邀請去給她的演講提意見時,我才明白為何柴靜要花一年時間,為何要采訪那么多人。
“聽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間,我覺得對她沒有任何期望,健康就好。但是,她被診斷為良性腫瘤,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術。”
我驚住了。
我做了那么多的大氣污染健康效應的報道,我知道空氣污染可以導致肺癌、心血管疾病甚至過早死亡,但已有的研究在我眼中似乎都只是數(shù)字,霧霾天我自己也不采取任何防護措施。
而柴靜的女兒,這個在2013年1月那場侵襲25個省市的大霧霾中被懷上的小生命,居然一出生就被診斷為腫瘤。那些空氣污染致病的概率似乎一下子變成了100%,我才明白為何柴靜如此認真的去尋找霧霾元兇,正如她所說,這是一個母親與和霧霾之間的私人恩怨。
那次模擬演講結束后,柴靜問我,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。我說,應該是柴靜女兒一出生就得了腫瘤,她懷疑和霧霾有關。
柴靜嘆了口氣,她說這也正是自己擔心的。她的家人其實很支持講出孩子的故事。但是從一個新聞從業(yè)者的角度出發(fā),柴靜覺得,從一個受害者角度出發(fā),可能有違客觀性。
我說,正因為你是一位受害的母親,才會有尋找答案的動力,去了解霧霾的健康危害,了解霧霾的原因和治理。我們不強調(diào)空氣污染和女兒的腫瘤之間的因果關系,但空氣污染的確會導致健康風險,雖然這種風險還有太多的未知,而這種未知更值得我們?nèi)グl(fā)現(xiàn),去呼吁,去阻止。
所以,在柴靜的片子中,最觸動我的場景便是她的小女兒,扎著倆小辮,伏在窗前,看著霧霾籠罩的世界。
臨走前,柴靜說,我一直在猶豫要不要放女兒的故事。這個猶豫一定會持續(xù)到片子錄制之前。
2015年1月27日晚上11點,白色絲質(zhì)襯衫,淺色牛仔褲,平底皮鞋。柴靜以一個母親普通的裝扮,完美的完成了演講。
無數(shù)臺攝像機,黑色大屏幕,全程無人發(fā)微博、朋友圈,我坐在小劇場的地上,和數(shù)百人,靜靜的、秘密的觀看了這場演講。
演講依然以女兒的故事開始,我內(nèi)心居然一下子釋然了。
柴靜張嘴就是“空氣動力學直徑小于2.5微米”,這一句對于PM2.5的定義體現(xiàn)了極強的專業(yè)性。而一束光打下來,她雙手捧著這些看不見的顆粒,又像一場感性的訴說。
她 真是太會講故事了,全程不超過三個磕碰。而這可是相當專業(yè)的故事,雖然是第二次聽,出于職業(yè)習慣,我居然還是記滿了三頁筆記,并標記出幾個小錯誤供后期修 改。她記下了那么多的數(shù)字,還要用形象的比喻描述出來。我深知這種難度,因為我在用文字描述的時候都極其困難,而她要講出來,甚至做出動畫表達出來。
片子分為三個章節(jié),霧霾是什么?從哪里來?我們怎么辦?
這是典型的專業(yè)報告結構,可是現(xiàn)場的觀眾似乎在尋求這種專業(yè)。我旁邊的小伙子在演講開始前問我機動車到底對于PM2.5貢獻多少,當柴靜說到這里時,他緊縮眉頭,頻頻點頭。而像邢臺市的“為我市退出全國74個城市空氣質(zhì)量排名倒數(shù)第一而喝彩!”的橫幅出現(xiàn)時,現(xiàn)場一陣笑聲。當APEC藍下的故宮角樓出現(xiàn)時, 那種稍縱即逝的美好使得包括我在內(nèi)的很多人,偷偷的舉起手機拍照。
回去的路上,我和幾個小姑娘同行,大家激動的表達觀后感。一個女生說,等片子出來后,我都已經(jīng)想好怎么宣傳了:如果你不想花時間看這幾年霧霾的報道,花兩個小時看這個視頻就夠了。
我說,你意思是我這三年多的報道都白寫了啊。
其實我的心里更為激動,大學里學習環(huán)境科學,畢業(yè)后從事環(huán)境報道,尤其是從事大氣污染報道,我看到了這種轉變。這種轉變不只是重腕治霾的“氣十條”,不只是全球皆知的“APEC 藍”,而是猶如那些彌漫在全國各地的細小的污染顆粒,對于空氣污染的關注也滲入了我們的生活,改變了我們。
正如2011年潘石屹轉發(fā)美國大使館監(jiān)測PM2.5數(shù)據(jù),接受外媒采訪居然還“受到了批評”。而今,賈樟柯拍《人在霾途》,柴靜講述自己的故事,甚至連過年回到家,家人都勸我離開那個“成天霧霾”的北京。
此刻,我在南京的火車站等候回京的列車,天氣陰冷,好在PM2.5只有十幾,空氣質(zhì)量優(yōu)。手機已被柴靜的視頻刷屏,一位在環(huán)保部門工作的同學發(fā)來消息稱贊這個視頻:“大家表示做得很到位”。
那就好。看吧,不在霧霾天發(fā)出也會有好效果的。
我想,柴靜今晚可以睡個好覺了吧。
“人去做什么,是因為心底有愛惜”
記者:你告別央視之后,為什么選了霧霾這么一個題材?
柴靜:這不是一個計劃中的作品,當時因為孩子生病,我辭職后打算用相當?shù)囊欢螘r間陪伴她,照顧她,所以謝絕了一切工作邀請。照顧她過程中,對霧霾的感受變得越來越強烈,整個生活都被它影響了,加上全社會對空氣污染問題也越來越關心,職業(yè)訓練和母親本能都讓我覺得應該回答這些問題:霧霾是什么?從哪兒來?該怎么辦?所以就做了這個調(diào)查。
記者:你怎么想到公之于眾的?
柴靜:一開始沒有想要公開,只是自己找資料,找專家問,想解開一些迷惑。我調(diào)取了十年來華北上空的衛(wèi)星圖片,可以看到空氣污染早已存在。我就在北京生活,怎么沒意識到?我找了奧運空氣質(zhì)量保障小組組長唐孝炎院士,她提供給我2004某個月的PM2.5數(shù)據(jù)曲線,相當于今天的嚴重污染,首都機場也關閉了,只是當天新聞報道是霧。可見當時整個社會對空氣污染缺乏認識。
我深感作為傳媒人的一員,也有責任,因為當時我在北京,但我渾然不覺。我做過不少污染報道,總覺得好象看到煙筒,看到廠礦才會有污染,所以生活在一個大城市里就無知無覺。
人都是從無知到有知,但既然認識到了,又是一個傳媒人,就有責任向大家說清楚。不聳動,也不回避,就是盡量說明白。因為如果大家低估了治理的艱巨和復雜,容易急,產(chǎn)生無望的情緒。如果太輕慢,不當回事,聽之任之,更不行。所以盡可能公開地去說明白,也許可以有很多人象我一樣有改變,為治理大氣污染做一點事。
記者:除了這次演講,你還做了什么?
柴靜:當前《大氣防治法》正在修訂,我將采訪的資料和稿件都發(fā)給了全國人大法工委,希望能為法律修訂帶來一點參照。他們逐字看完,附上建議,返還給我,并打電話表示感謝,說會在修訂時考慮相關問題。
我將稿件也發(fā)給了正在制訂國家油氣體制改革方案的小組成員,得到的反饋也讓我很意外。他們提出的唯一意見是,如果篇幅不限,可以談得更多。
我想立法者和政策制訂者的態(tài)度是因為,改革在中國適逢其時,需要讓大眾更多地知情參與,更多地討論,形成共識。公眾是空氣污染治理的核心力量之一,沒人比普通人更清楚自己身邊的污染源,也沒人比我們更愛護自己的家園。
記者:一個母親這個身份切入,我是覺得特別親切,但是你有顧慮嗎?
柴靜:我有一個很大的顧慮,就是說我有沒有權力說到她?因為那是她的生命和她的生活,我必須要考慮說出來之后她將來可能會承受什么,這種壓力最大。后來我先生說,你還是說吧,我最深刻地感覺到你在有孩子,尤其她生病后,才會對空氣污染這件事有了完全不同的態(tài)度。他說,這是你回避不了的一個基本動機。 他說,如果你回避了她生病,這種態(tài)度里面其實隱含著一個問題,就是說好像生病本身是不好的,或者是羞恥的。不用太顧慮和緊張,要相信這個社會的基本善意。這句話對我有說服力。
記者:這次的拍攝費用大概多少?是誰投資的?
柴靜:差不多一百萬吧,因為有國內(nèi)外的拍攝和后期制作的費用。錢是我自己投的,國內(nèi)一些基金會聯(lián)系過我,愿意資助,但我當時完全不知道自己會做成什么樣子,又要照顧孩子,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做完,就沒接受,非常感謝他們。我兩年前出過書,用稿費負擔的。
記者:你是成立了個人公司制作節(jié)目嗎?
柴靜:沒有,這次只是個人調(diào)研,播出也是公益的。跟我一起做這件事情的,是我的幾位朋友,老范、番茄、螞蟻、三三、席大、晨超、五號、子雄、家賢、念念、小米,十人左右,甘苦與共。沒有他們,就不會有這件事,我非常幸運。如果將來有機會,希望仍能與他們一起,為轉型中的社會做一點紀錄和分析的工作。
|
|